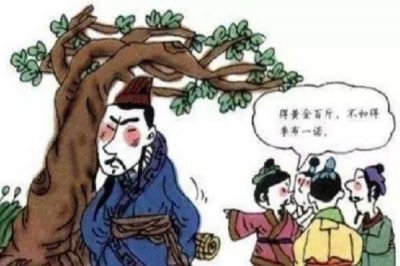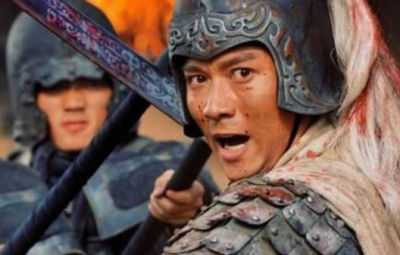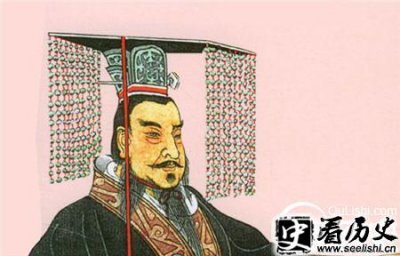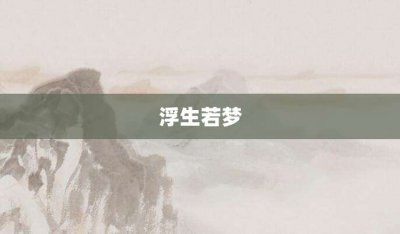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农民起义军出身的女皇帝——文佳皇帝陈硕真
其实关于中国历史上到底有多少个女皇帝,不少文章早就有定论。不过,西辽并非中国政权,由于蒙古人灭西辽后,占据西辽的地方建立察合台汗国,而四大汗国具有主权上的独立性,西辽土地并未进入元朝领土之内,因此西辽并非中国的政权,尽管西辽行使辽制,而辽国基本被认定为中国的朝代。耶律普速完是否是中国的皇帝都存在疑问,自然不能算入毫无争议的中国女皇中。
我们在这里并不过多去探讨这个问题,但是另外三位女皇,除了北魏的元氏为傀儡皇帝外,实权派人物只有武则天和陈硕真。当然,在中国历史上唯一正统的女皇帝只有则天皇帝武曌。不过,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不是武曌,而是文佳皇帝陈硕真。
陈硕真,一作陈硕贞,睦州雉山梓桐源田庄里(今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梓桐镇)人。和其他“乱臣贼子”不一样,陈硕真是一名女性。这种情况恐怕只有开放的唐朝才会出现。
01.
浙江为何会爆发如此影响巨大的民变?
陈硕真的起义爆发于永徽四年(653年),其实史书对于陈硕真的记载非常之少。《旧唐书》的本纪里仅有只言片语:
(冬十月)戊申,睦州 女子陈硕贞举兵反,自称文佳皇帝,攻陷睦州属县。婺州刺史崔义玄、扬州都督府 长史房仁裕各率众讨平之。
连起义镇压下去的时间都没有。
《新唐书》本纪中的记载倒是详细一些:
(冬十月)戊申,睦州女子陈硕真反,婺州刺史崔义玄讨之。十一月庚戌,陈硕真伏诛。
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次起义,史书压根就没有记载。
一般情况下,《资治通鉴》及会有更详细的记载,于是笔者又翻阅《资治通鉴》,果然,更详细的记载出现了:
初,睦州女子陈硕贞以妖言惑众,与妹夫章叔胤举兵反,自称文佳皇帝,以叔胤为仆射。甲子夜,叔胤帅众攻桐庐,陷之。硕真撞钟焚香,引兵二千攻陷睦州及於潜,进攻歙州,不克。敕扬州刺史房仁裕发兵讨之。硕真遣其党童文宝将四千人寇婺州,刺史崔义玄发兵拒之。民间讹言硕真有神,犯其兵者必灭族,士众凶惧。司功参军崔玄籍曰:“起兵仗顺,犹且无成,况凭妖妄,其能久乎!”义玄以玄籍为前锋,自将州兵继之,至下淮戍,遇贼,与战。左右以楯蔽义玄,义玄曰:“刺史避箭,人谁致死!”命撤之。于是士卒齐奋,贼众大溃,斩首数千级。听其余众归首;进至睦州境,降者万计。十一月,庚戌,房仁裕军合,获硕真、叔胤,斩之,余党悉平。义玄以功拜御史大夫。
《通鉴》详细记述了起义被镇压的全过程:
陈硕贞妖言惑众,和妹夫章叔胤造反,自称文佳皇帝,章叔胤为仆射。章叔胤攻陷桐庐,陈硕真撞钟焚香,带两千军攻陷睦州、於潜,但是在进攻歙州时没有攻克。皇帝下诏命扬州刺史房仁裕征讨。陈硕真派手下童文宝率四千人攻打婺州,婺州刺史崔义玄抵抗。民间传说陈硕真有神仙(保佑),如果跟她的士兵冲突必定会身死族灭,于是唐朝的士兵害怕。
参军崔玄籍认为陈硕真打仗很顺,都能一事无成,更何况只凭借妖言邪说,怎么能长久呢?于是崔义玄让崔玄籍为前锋,自己率领州兵跟进,到了淮戍,和陈硕真军遭遇,于是打起来了。手下用盾遮蔽崔义玄,崔义玄说:“刺史躲箭,谁还愿意上阵送死?下令撤掉盾。于是士气大涨,陈硕真军溃散,斩首数千级。任由其他人归降自首,军队到了睦州,降者数以万计。十一月,同房仁裕军会合,抓住陈硕真、章叔胤,斩首,余党都被平定。
但是同样的,陈硕真为何会造反,仍然没有答案。陈硕真造反之众按照这个记载,起码数以万计,光看这个数字,只能推测出两种可能:
陈硕真真的用妖言惑众。官逼民反。
另外两唐书的崔义玄传都有记载,意思差不多:
属睦州女子陈硕真举兵反,遣其党童文宝领徒四千人掩袭婺州。义玄将督军拒战,时百姓讹言硕真尝升天,犯其兵马者无不灭门,众皆凶惧。司功参军崔玄籍言于义玄曰:「起兵仗顺,犹且不成,此乃妖诳,岂能得久?」义玄以为然,因命玄籍为先锋,义玄率兵继进,至下淮戌,擒其间谍二十余人。夜有流星坠贼营,义玄曰:「此贼灭之徵也。」诘朝进击,身先士卒,左右以盾蔽箭,义玄曰:「刺史尚欲避箭,谁肯致死?」由是士卒戮力,斩首数百级,余悉许其归首。进兵至睦州界,归降万计。及硕真平,义玄以功拜御史大夫。——《旧唐书》
时睦州女子陈硕真举兵反。始,硕真自言仙去,与乡邻辞诀,或告其诈,已而捕得,诏释不问。于是姻家章叔胤妄言硕真自天还,化为男子,能役使鬼物,转相荧惑,用是能幻众。自称文佳皇帝,以叔胤为仆射,破睦州,攻歙,残之,分遣其党围婺州。义玄发兵拒之,其徒争言硕真有神灵,犯其兵辄灭宗,众凶惧不肯用。司功参军崔玄籍曰:「仗顺起兵,犹无成;此乃妖人,势不持久。」义玄乃署玄籍先锋,而自统众继之。至下淮戍,擒其谍数十人。有星坠贼营,义玄曰:「贼必亡。」诘朝奋击,左右有以盾鄣者,义玄曰:「刺史而有避邪,谁肯死?」敕去之。由是众为用,斩首数百级,降其众万余。贼平,拜御史大夫。——《新唐书》
在《新唐书》中还记载了陈硕真的妖言:
说自己即将成仙,和邻居辞别,有人告她欺诈,抓住后,皇帝下诏释放不问。章叔胤说陈硕真从天上回来了,而且变成男子,会各种法力,行踪不定,于是老百姓上当受骗。由于当时人并不相信官方说法,各种民间传说纷至沓来。

陈硕真
于是乎,出现了野史记载。
睦州陈硕真,新安县人,身颀皙,美姿容。侠肝义肝,矫捷善斗。硕真时年廿一,与其夫率乡众抗苛赋,夫亡,硕真逃遁,入庵为尼。多年后得异人传《无生圣母秘本阴符火凤经》,入深山潜修数年,称已得道。出山行游乡县,神治时行疟疾,用一个灵符,念无生圣母经,疟疾立刻就好。所到之处信众如云,皆以师礼事硕真。硕真创火凤圣教,自号赤天圣母。三更静夜裸身登坛,曰:或是男、或是女,本来不二,都仗着无生母,一气先天。咒诅盟誓,以密传口诀。
永徽三年,睦州三月不雨,田野龟裂,蝗虫蔽日,饿殍遍地,新冢累累。硕真时年三十三,僭称文佳皇帝,(另有版本为“
睦州陈硕真,新安县人,身颀皙,美姿容,而矫捷善斗,力能举千斤。年长不嫁,有求之者,则曰:九天玄女授我神力,能胜我即许之。乡里鬨动,与角者甚众,而硕真未尝一败。中有勇力过人者,尽收为羽翼,以师礼事硕真。
永徽三年,睦州三月不雨,田野龟裂,蝗虫蔽日,饿殍遍地,新冢累累。硕真时年廿一,创火凤社,自号赤天圣母“)
曰:官府无道,上苍震怒,降此灾劫,尔等当从我之道,揭竿而起。一时从者逾千,竹木为帜,锄耙为械。入新安,斩命官,各县来投者万人。遂攻睦州,陷之,又分兵取歙、婺,举朝震惊。上命长史房仁裕、刺史崔义玄举兵平之。长史至,先遣使招硕真来降。硕真曰:“我岂屈膝事人者?”乃毁书斩使,尽起睦州军,以姻家章叔胤为仆射,引前军迎长史,自引后军应之。前军遇长史于桐庐,战方酣,叔胤困于阵中,硕真至,急麾军救之,恃勇决围出。遁返睦州,前军尽没。长史进围睦州,攻打甚急。硕真语其众曰:“歙、婺之徒后日至。”后日不至,则复语后日,如是者再三,众始疑之。叔胤昼夜登城守御,流矢贯脑门而死。硕真既丧至亲,又有兔死狐悲之慨,哀恸不已。然勒众愈戾,有稍不当意者辙斩之,众怨怼日甚。初,其徒童文宝尝以小故见责,已为长史暗细许以官爵,重金收买。至此托言解忧,进醇酒于硕真,意将伺机鸩之。硕真斥退文宝,自取酒痛饮竟夜,不觉大醉,从人舆置榻上。文宝窥见,即入室尽杀从人,就榻上擒硕真,开门献于长史,余众皆降,乱遂平。
硕真见长史,抗辞激烈,绝无悔意。长史大怒,令军吏褫其衣棠,褪其鞋袜,去其亵裤,裸缚刑堂。硕真虽三十有三,久修男女双运,肤若处子也。长史阴使军吏极尽凌虐,严施酷刑。硕真凄号不止,死去活来,绝无悔意。长史解硕真还扬州,驰书告捷,后数日,上有旨曰:新安县易名还淳,硕真就地剖决,以绝其患。
十一月庚戌,长史令剖硕真于文选楼前校场。辰时,先遣人婉言谕硕真,谓剖刑不过一刀之厄,以安其心。硕真信之,乃自裸上身,袒玉乳如钟,皂吏背缚之,引硕真自牢中出。硕真面无惧色,昂然自行。出门忽见一木车,上有杵粗如儿臂,有机括连于车轮,推动时,其杵上下攒动,名曰木驴,实天下第一辱刑也。街中观者如堵,蚁聚于道,硕真始知其刑之辱,急以双足勾门前牵马柱,不行,曰:“速杀吾。”众吏强之,不可脱,以梃击硕真足,硕真忍痛不动。又令数人牵硕真足,终不可分。或禀长史,长史阴使人猝击硕真乳,硕真惊惶稍懈,双足始为吏所分。又以长绳分系硕真双足,虑其故伎重施也。硕真自度终无计可免辱,故不复拒之。皂吏褪其鞋袜,褫其下裳,去其亵裤,露天足似白莲,现粉尻似满月,展墨草似幼兰,肌肤如玉,娇颜胜火,旖旎已极。又举硕真示众,分赛雪双股,张如花牝户,众皆喝彩,硕真大羞,不敢仰视。然后置硕真木驴上,伸杵入牝户中,推车遍游六街三市,车行则杵动,深深浅浅,吞吞吐吐,极尽妙趣。硕真犹处子也,为巨杵所淫,自辰至巳,苦乐难耐,呻吟不已。观者戟指笑骂,不一而足。更有登徒子趋之若骛,以手捻其乳摩其尻为乐,硕真不甘,扭躯相避,则牝户中痛痒愈甚,虽瞑目不视,而忸怩万状,虽咬牙不语,奈何丑态百出焉。
午初,车至文选楼,有台高丈二,立刑柱一双,市井之民摩肩接踵,熙熙攘攘,争睹硕真。吏掳硕真台上,展其肢如大字,缚手足于柱上,硕真始张目舒气,神色稍定。仰天呼曰:“无生母,文佳愿代天下苍生受一切苦,文佳浑身碎骨,火凤圣教永不灭绝!”
午正,长史掷火签于地,刽子以六寸大钉钉硕真手足于刑柱,硕真手挣足挺,惟坚忍不作哀声,目视长史詈之不已。刽子以利刃割硕真玉乳,分投台下,好事者奔走抢夺,喧闹震天。又以小钳尽薅其阴毛,状如白虎者。又引刀自牝户入,裂其会阴,使与后窍通,粪尿喷出,秽臭四溢。又割其阴器,以手细剖其子孙道,持之示众。硕真羞极恨极,痛极怒极,双目尽赤,号呼不止,声如屠豕。然后上割至膈,雪腹裂如剖瓜,柔肠尽泄,血流如注。---取其脏腑,唯留心肺以延残喘。其时硕真双唇尚翕张欲语,惟胸脯已破,喉中哑然,但怒目横视而已,意似示不屈者。
须臾,硕真犹仰首瞠目,然手足尽舒,气已绝矣。长史令刽子以巨斧割首级函于匣中,驰送京中献于陛前。又截其四肢,号令四门。十日后,收聚硕真残躯,醢之焚之,扬灰于东海之滨。唯遍访硕真双乳不获,或曰其一得之者以百金售于某贾,贾已食之矣。
呜呼!观硕真志存于天下,而才止于惑众,勇可敌万人,而败于一匹夫之谋,盍志大才疏,有勇无谋耶?其败也必矣。然斧钺加身,九死不悔,盖亦女中之雄也!可怜得志于旬月之间,逞威于弹丸之地,而丧身于万众之前,备极凌辱,尸首难完,诚足为谋逆者戒!
——唐·无名氏《陈硕真传》
由于这段记载如果翻译过来会过于血腥,因此笔者不在这里做全文翻译。笔者只说明一下这里面的一个重要信息,那就是,陈硕真到底为什么造反。
在野史中,睦州三个月不下雨,田地都龟裂了,蝗虫多得能遮蔽太阳,黑压压一片,饿死的尸体到处都是,新坟也到处都是。于是陈硕真将天灾的责任归于官府,说官府无道,上天震怒,所以降下此等灾祸。所以得造反。
不管是正史还是野史,陈硕真虽然造反的理由不同,但说的话都是“妖言”。天灾降下,是因为官府无道,先不说这个逻辑是不是涉及迷信,在中国古代这种逻辑实际上是正确的,但是接下来应该是什么?官府无道那就应该由皇帝撤换地方官,并自省己过,再前往佛寺祈祷求雨,这才是正常的解决问题的渠道。但是陈硕真就是以上天降灾为由,就要造反。但是当时的皇帝唐高宗在长孙无忌的辅佐下并无过失,无论如何都不至于去推翻唐朝。
实际上,不管陈硕真起义的理由如何,野史中,陈硕真叛逆的一面都在年轻时一一展现,陈硕真有神力,于是吹牛说自己是九天玄女传授的神力,非能力气大过她的男人不嫁。后来又和丈夫一起率众逃苛捐杂税,失败后丈夫失踪,自己逃到尼姑庵李出家。又创立邪教。可见,不论正史野史,都妖魔化了陈硕真,不同的是野史对陈硕真的起义抱有同情态度,也因此才会描写陈硕真所受酷刑。
不过,野史记载除了遇上旱灾,老百姓因此饿殍遍野,所以造反相对合理,其余记载均不合理。唐朝酷刑之中,没有将人剖腹、割乳的刑罚。不仅《唐六典》无记载,就连《永徽律》也没有任何记载。而除了皇帝,没有地方官能越过法律做事,处置犯人更需要按照法律来。而且,中国古代对女犯人的刑罚也非常轻,一般只有夹棍等,目的是让女子无法再做女红,以此羞辱,女子犯罪连刑具都不需要戴,更何况是野史中记载的酷刑?而这本《陈硕真传》距离陈硕真造反的时间非常之久,作者又怎会知晓陈硕真创立的邪教名字叫火凤社?往往说得越具体,史书的水分就越大,整个野史就像小说的笔法,让人不得不怀疑真实性。

陈硕真起义
02.
起义原因真相
其实,不论官方记载还是野史记载,可信度都有限,统治者为了维护纲常秩序,自然是需要抹黑起义者,而对自己的过错三缄其口。野史中关于旱灾和蝗灾引起造反虽然符合历史发展规律,但是如此大规模的旱灾和蝗灾只在一州之境出现,并且没有瘟疫蔓延至各地,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。
那么陈硕真为何造反?正史中是毫无线索的,但是野史中提供了两条线索:一是陈硕真打出的旗号“官府无道”,二是陈硕真曾经率众躲避苛捐杂税。也就是说,苛捐杂税很可能是引发大规模叛乱的原因。
那么究竟是不是呢?
首先讲到税,必然要翻阅《唐会要》。《唐会要》的卷八十三有记载唐朝的税制。
租税上旧制。凡赋役之制有四。一曰租。二曰调。三曰役。四曰杂徭。开元二十三年敕。以为今天下无事。百姓徭役。务从减省。遂减诸司色役一十二万二百九十四人。
……
贞观十一年。侍御史马周上疏曰。自古明王圣主。虽因人设教。宽猛随时。而大要惟以节俭于身。恩加于人。二者是务。今百姓承丧乱之后。比于隋时。才十分之一。而供官徭役。道路相继。兄去弟还。首尾不绝。春秋冬夏。略无休时。陛下虽每有恩诏。令其减省。而有司作既不废。自然须人徒。行文书役之如故。臣每访问。四五年来。百姓颇有嗟怨之言。以为陛下不存养之。今京师及益州诸处。营造供奉器物。并诸王之服饰。议者皆不以心俭。陛下少处人间。知百姓辛苦。前代成败。目所亲见。而犹如此。而皇太于生长深宫。不更外事。万岁之后。固圣心所当忧也。凡修政教。当修之于可修之时。若事变一起。而后悔之。则无益也。故人主每见前代之亡。则知其政教之所由丧。而皆不知其身之失。是以殷纣笑夏桀之亡。而幽厉亦笑殷纣之灭。京房云。后之视今。亦犹今之视古。此言不可不诫也。往者。贞观之初。率土荒俭。一匹绢才得一斗粟。而天下帖然。百姓知陛下忧怜之。故人人自安。曾无怨讟。自五六年来。频岁丰稔。一匹绢得粟十余石。百姓皆以为陛下不忧怜之。咸有怨言。以今所营为者。颇多不急之务故也。自古已来。国之兴亡。不由蓄积多少。唯在百姓苦乐。且以近事验之。隋室贮洛口仓。而李密因之。东都积布帛。而王世充据之。西京府库。亦为国家之用。至今未尽。向使洛口东都无粟帛。则王世充李密。未必能聚大众。但积贮者。固是有国之常事。要当人有余力。而后收之。岂人劳而强敛之。更以资寇。积之无益也。然俭以息人。贞观之初。陛下以躬为之。故今行之不难也。若人既劳矣。而用之不息。倘中国被水旱之灾。边方有风尘之警。狂狡因之以窃发。则有不可测之事矣。以陛下之明诚。欲励精为政。不烦远求上古之术。但返贞观之初。则天下幸甚。
……
永淳元年。太常博士裴守真上表曰。夫谷帛者。非造化不育。非人力不成。一夫之耕。才兼数口。一妇之织。不赡一家。赋调所资。军国之急。烦徭细役。并出其中。黠吏因公以贪求。豪强恃私而逼掠。以此取济。民无以堪。又以征戍阔远。土木兴作。丁匠疲于往来。饷馈劳于转运。微有水旱。道路遑遑。岂不以课税殷繁。素无储积故也。夫大府积天下之财。而国用有缺。少府聚天下之伎。而造作不息。司农治天下之粟。而仓庾不充。太僕掌天下之马。而中厩不足。此数司者。役人有万数。费损无限极。调广人竭。用多献少。奸伪由此而生。黎庶缘斯而苦。此有国之大患也。
贞观十一年,侍御史马周上书皇帝,称徭役繁多,百姓不堪其累,多有怨言。粮食贬值,倘若有一天有水旱灾害,必为大患。
永淳元年太常博士裴守真的上表更表明唐初的税制存在问题,粮食布帛每年年成不同,而当时已经到了一个男人种的地养不活一家数口,女子织的布帛,也不够一家人穿,但是赋税则是根据国家临时需求而定。我们知道往往老百姓越穷时政府需求也更多,再加上各种劳役已经到达“烦徭细役”这么多。而官吏借着公务层层盘剥百姓,地方豪强更是直接恃强凌弱进行抢掠。
每丁岁入租粟二石。调则随乡土所产,绫、绢、絁 各二丈,布加五分之一。输绫、绢、絁者,兼调绵三两;输布者,麻三斤。凡丁, 岁役二旬。若不役,则收其佣,每日三尺。有事而加役者,旬有五日免其调,三旬 则租调俱免。通正役,并不过五十日。若岭南诸州则税米,上户一石二斗,次户八 斗,下户六斗。——《旧唐书·食货志上》
租庸调之法,以人丁为本。——《新唐书·食货志二》
两唐书关于税收方式的记载更为详细,由于这并非本文研究方向,只简单说一下唐初税制,即按照户型(不是富人为上户,穷人为下户),根据这个来收取租、庸、调。而户型划分并不是按照平均每人的财富多少,而是按照人丁多少,而上户人丁是最多的,而土地多少则按照人口多少来分配。不同年龄、性别的人,给不同的土地。
然而,土地的优劣、以及每年气候的影响,唐朝政府基本无视。
结合野史中苛捐杂税的记载,两相映证,可见,当时极有可能是好几个州的百姓都遭遇了旱灾。不然,婺州也不会有关于陈硕真的兵有神仙相助,跟她打要灭族的传言,而一州经过旱灾饿殍遍野,剩下的男丁也不够陈硕真帐下几万人的。(这里依据正史)

陈硕真
03.
起义为何失败?又该如何评价?
其实,陈硕真起义失败,除了唐朝气数未尽之外,还有一点就是陈硕真手下的士兵和将领都是平民出身,不会打仗。这里我们将江南东道的地图摆出来供大家一观,如果看不清可下载放大:

江南东道地图
陈硕真先打下桐庐(睦州境内),随后攻下睦州。然后攻下于潜(杭州境内),之后打、歙州、婺州,我们就把桐庐当成她的根据地,然后她向西南攻下睦州,然后睦州府全境未攻下,又向北打杭州的于潜。之后不打杭州府,却去打西北方向的歙州,打不下来,就去打东南的婺州。整个行军极其混乱,根本没有一个军事方针,一个重要的州都没打下,事实上,如果非要打婺州,于潜打下后应该继续向东攻打临安、杭州、新城、余杭,随后打越州、明州诸县和州治,南取台州,之后向西攻衢州,再南下括州,这些州的兵力配给稍差,且能形成对婺州的合围。即使不想死磕婺州,也应该向东打,形成根据地。
起义军缺乏地盘,即使真不想这么打,也应该死磕歙州,而不是打一半,那边明明快要支撑不住了,这时候却不打了,换个地方打。搞得自己兵困马乏,而对手以逸待劳。
陈硕真的起义,凸显了官僚系统的问题,因此才有后来大臣的上疏。当时没有形成普遍的反抗,遍地都是蜂拥而起造反的反贼,也是因为当时唐朝的政策还只是弊政,而非暴政和急政。而当时的灾荒也没有到处都是,也没有昏君出来祸国殃民,所以没有一个导火索引发更大的叛乱。因此,这次起义注定失败,但也让之后的唐朝注意到了一些问题,并从中吸取教训,为武则天后来缔造武周盛世创造了一定的条件。
参考文献:《旧唐书》、《新唐书》、《资治通鉴》、《陈硕真传》、《永徽律》、《唐六典》、《唐会要》、谭其骧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